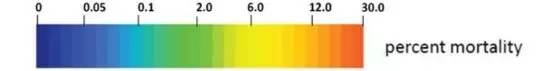过林卡的人都要带上酥油茶和奶茶,这是他们日常最喜爱的饮品。
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的茶,原产于我国。据记载,早在3000多年前的周代我国已产茶。由于生息于这一得天独厚的茶的故乡中,我国各民族人民绝大多数都有饮茶的习惯,但把茶作为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的,则首推藏族。藏族人对茶的至爱至嗜,大概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比得上。对于藏族来说,茶是“生命之源泉,天神所赐的甘露”,像空气、阳光、食粮一样,终生不能相离,饮茶如同吃饭一样重要,不分男女、老幼、僧俗、贵贱,“无人不饮,无时不饮”。由此而形成的藏族茶文化更是多姿多彩,绚丽璀灿,成为世界茶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大凡一种饮食习惯的形成,总依赖于所处客观环境提供的物质,而藏族居住区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干燥、酷寒、素不产茶,为何这里的人们养成了如此强烈嗜好的饮茶习惯呢?于此有必要对藏族饮茶习惯形成的历史过程作一些探讨。
我国的茶原产于南方,其中巴蜀和云南是最早产茶、饮茶之地。顾炎武《日知录》说:“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认为中原饮茶是秦由蜀传去的。巴蜀不仅产茶早,而且是最先把茶作为商品上市交易的地区。西汉王褒《僮约》中记载蜀西民间贸易活动说:“牵犬贩鹅,武阳(今四川彭山县境)买茶。”说明至少在西汉时蜀人已将茶作为商品。据《史记》、《汉书》等记载,西蜀的商人秦汉之时已与康藏高原东部的都夷、牦牛夷等有着交换关系,以蜀中之茶换取马、牦牛等。茶这时既已成为蜀中的商品,自然会在这种交换中输入高原东部地区这些藏族先民之中。不过,限于历史条件,当时产茶不多,即在内地尚未形成普遍的饮茶习惯。高原上的藏族先民当然更无饮茶的习惯。
据藏文史籍记载,茶正式输入西藏是在吐蕃王朝的都松莽布支赞普时期(676-704年在位)。当时体弱多病的赞普偶然捡到小鸟衔来的一支树枝,随手扯了几片绿叶放入口中嚼,顿觉神清气爽,身体轻快,于是命大臣无论如何要找到这种树叶。后来大臣在汉族地区找到这种树叶,才知是茶,带回献给赞普,赞普经常食用,身体逐渐好了起来,于是茶便成为吐蕃宫廷一种珍贵的保健药物。这种把茶当作保健药物的情况,与内地最早对茶的认识是一样的。《神农本草》载:“神农氏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神农食经》说:“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都是看重茶的医疗保健作用。藏族地区高寒缺氧,食物又是牛羊肉和糌粑等油、燥性之物,缺少蔬菜。茶中富含茶碱、单宁酸、维生素,具有清热、润燥、解毒、利尿等功能,正好弥补藏族饮食中的缺陷,防治消化不良等病症,起到健身防病的作用。因此,藏族人最初仅把茶作为一种保健药看待就不足为怪了。不过,在吐蕃王朝的前期,由于汉藏贸易尚不发达,由内地输入藏区的茶还很少,只能供王室和贵族享用,藏族人民生活中还无饮茶之习。
唐李肇《国史补》记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乾者。’”这里所说的常鲁公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奉使入吐蕃议盟的监察御史常鲁。唐自开元后,士大夫中盛行烹茶之艺,烹茶时要加入姜、盐和各种辛香之物以调味,吐蕃赞普见而奇之,不知所煮为茶,这说明当时吐蕃尚不知唐人烹茶之方法,也还未把饮茶作为一种生活享受。再看赞普拿出的茶中,尽是当时天下名茶,寿州、舒州者,指安徽的小围、六安茶;顾渚者,指浙江的紫笋茶;蕲门者,指湖北的黄芽茶;湖乾,指湖南的银毫茶;昌明者,指蜀中绿昌明茶。吐蕃宫中收藏了这许多唐之名茶,却又不晓唐之烹茶方法,正好印证了藏文史料中的记载,说明当时茶还是被当作珍贵的保健药而被王室收藏,并未成为广大藏族人生活中的饮料。
在敦煌千佛洞和新疆地区出土的一批吐蕃时期的历史文书、木简中,记载了吐蕃社会的经济生活情况,但在这些于8-9世纪的文献中,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物资有青稞、小麦、酒、皮张、牲畜等,却单之不见有茶,这说明至少在9世纪初以前,茶还没有进入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社会上还没有饮茶之习。
藏族民间饮茶大抵在9世纪初以后才开始,这是因为从初唐到中唐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期中,虽然因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开辟了唐蕃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渠道,推动了藏汉贸易的发展。但总的说来,唐蕃因争夺势力范围的冲突时有发生,争战连绵,在大多数时候双方的贸易关系不能正常开展,这就极大地制约了茶对藏区的输入。所以吐蕃虽很早就输入了内地的茶,但都没有使茶在吐蕃社会各阶层中传播,更没有使饮茶成为一种全社会共同的生活习惯。
晚唐以后,唐蕃双方进入了一个较稳定的和睦相处时期。从而使汉藏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了长足的进展。战争状态的结束,使官方和民间的商贸渠道都畅通无阻,这就为茶大量输入藏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给藏族饮茶之习的形成提供了物资基础。
另一方面,晚唐时期吐蕃的社会环境也为饮茶之习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吐蕃的热巴巾赞普(815-838在位)开展了空前的尊佛运动,规定了七户养一僧的制度,藏地的僧人从此脱离生产劳动,专事修习,对于每日打坐诵经的僧人来说,茶的“破睡”和“涤烦疗渴”作用尤显得突出。唐朝自开元后,因禅宗盛行,坐禅之人“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封氏风闻录》)。
吐蕃在弘佛时,曾有大批汉族禅僧来藏传法,他们将内地烹茶的方法和坐禅饮茶的习惯首先传给了藏地的僧人。由于藏族对僧人(喇嘛)十分崇敬,他们的饮茶习惯极易被人效法。特别是吐蕃最后一位赞普达玛(839-842在位)时大力灭佛,寺院被毁,大批僧人被迫还俗,这些融入民众中的僧人又将饮茶之习和烹茶之法直接传播于普通的人民之中。在物质生活处于相当低下水平和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人们的物欲受到相当大的抑制的氛围中生活的藏族人,茶除了能满足他们生理上的需要外,还能给他们带来心理上享受,填补生活中的一些缺憾。因而,饮茶就从功利需要的基础上更衍生了认识需要、审美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怀特所说:“文化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需要。”饮茶作为一种文化就这样在藏族中产生并发展起来。
藏族的饮茶之习既是汉藏人民经济交流的结晶,也是汉藏文化交流的结晶,虽然今天藏族的茶文化已是独具一格,带有显著藏民族特色的文化,但寻根究底,我们仍可在一些方面发现汉族茶文化的印痕。据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藏族烹茶之法原从汉地和尚学来。我们把藏族烹茶之法和唐宋时内地烹茶之法相比较就不难发现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唐陆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