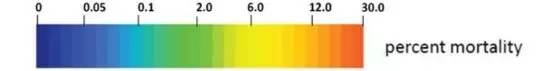2002年淮安美食节前夕,我们两人作为中国烹饪协会专家组成员,随中国烹饪协会特邀顾问、烹饪文化研究会会长、专家组组长林则普先生前往淮安鉴定授予江苏淮安“淮扬菜之乡”的申请。在从上海到淮安的路上,高成鸢将特地带来的一本书给李耀云翻阅。
那是台湾出版的已故著名作家高阳的一部饮食文化专著,书名是《古今食事》。其中题为《河工与盐商》的一章,以大量的史料说明淮扬菜的形成与豪奢饮宴的密切关系,而在这方面“河工”比盐商的表现更为惊人。
商阳号称“台湾的金庸”,著有《红顶商人胡雪岩》等十来部历史小说,多以清代为背景,所以他对清史非常熟悉。同时他更对美食深有研究。书中提到,长驻淮安的河道总督衙门岁有经费450万两,最多只需1/3,其余巨金“挥霍而已”。公开“公款消费”的官府只此一家,决非作为私人的盐商可比。饮宴不仅要有钱更要有闲,而河工每年只忙一季。
河工一场宴席要三天三夜,食客“从未有能终席者”。由此高阳提出了大命题:“我想,所谓‘满汉全席’,大概就是由河工上这须三昼夜才能吃完的筵席演变而来。”
“满汉全席”被公认是中国烹饪发展顶峰的标志。这样重大的文明成果是不会一下子冒出来的,在形成中必有其前身,前身之前还有前身。高阳从历史的角度在“满汉全席”之前特加“所谓”二字,是不无思考的。
从现有各家的专题论著来看,“全席”先前称为“大席”。例如王仁兴先生《中国饮食谈古》一书中的专文,题目即为《满汉全席》。“大席”之称当是由宫廷生活用语派生的,例如皇帝的婚礼叫“大婚”,宴席伴奏音乐叫“丹陛大乐”。如此,则认为满汉大席出自宫廷就容易理解了。但王仁兴先生通过考证首先否定了此说。认为大席出自官府,根据之一是最早记述这类宴席的袁枚《随园食单》:“今官场之菜……有满汉席之称。”
“满汉席”名目又来自“满席”和“汉席”的合称。据《大清会典》和《光禄寺则例》等书记载,清宫中有这两种宴席名目,自然也流行于官府。值得注意的是,袁枚在上引的语句中接着说,官府的满汉席除用于“新亲上门”外,也用于“上司入境”。最大的“上司”是皇帝,他的临幸,当然要享之以最大的“大席”。皇帝在外地可以留住不短的时间,那时他“驻跸”的官府便无异于行宫,官府宴则等同于宫廷宴。这该正是误认为满汉全席出自宫廷之说的原则。
“满汉全席”的形成,还有一个前身,就是“全羊席”。对清代烹饪文化有专门研究的吴正格先生的新著《中国京东菜系》中有个示意图,其中以“全羊席”与“满汉全席”双双并列。《清稗类钞》早已断言,“清江(淮安)庖人善治羊”,“号称一百零八品”。淮安独有的108品“全鳝席”,显然是从全羊席派生的。这都是“满汉全席”源于淮安的佐证。
吴先生书中称乾隆是“满汉全席”的“直接倡导者”。满度、汉席最早的合璧既然又不在宫廷,则最可能发生在淮安的河工衙门。据新出版的《淮安古迹名胜》,“清晏园”先前曾命名为“清宴园”,这个名称也使人联想到此园与盛宴的关系。
“满汉全席”声名大噪,是近代门户开放、市场经济繁荣后,餐饮业“炒作”的结果。其实早期记载满汉席的还有苏州人的著作《桐桥倚棹录》。我们认为这并不能证明“全席”源于扬州或苏州。较早的记载见于那些地方,是由于那里的文化和商业后来大大超过了淮安。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淮安城市的重要地位确是较早时期的事,对此淮安地方史的研究者们已有充分的论述,我们在此便不再赘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