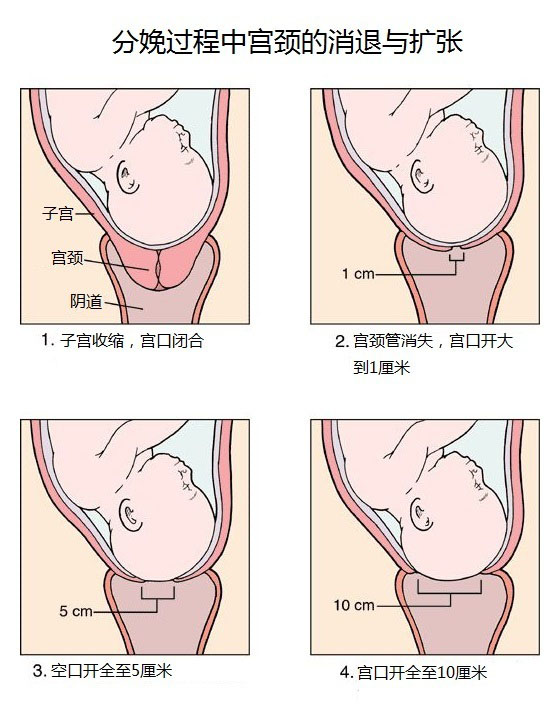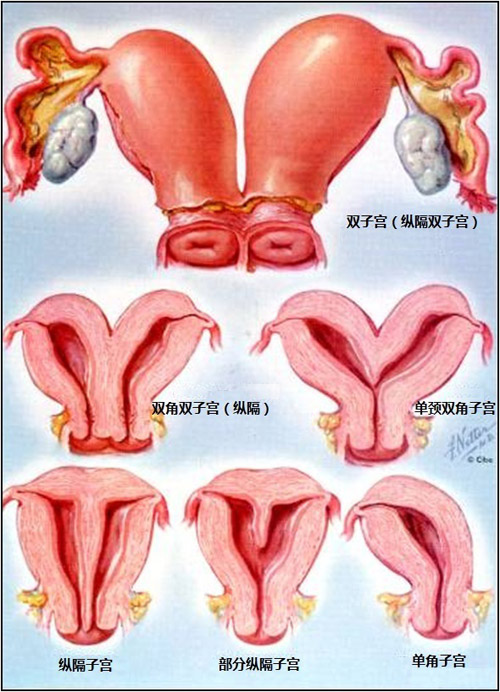一个在海外打拼的中国青年,在泰国感染艾滋病。9年后,他讲述了染病后的生活变故、人情冷暖和恐惧、孤独的生存状态。
一个大胆的女记者,贴身采访,穷追不舍,历时180个日日夜夜,记录了中国迄今最为完整的艾滋病个案。
就在完成一系列隐性采访之后,我决定关注艾滋病群落。
这个特殊群落正在逐步扩大,日渐影响正常人群的生活。
2000年4月中旬,我去深圳市卫生防疫站HIV抗体确认室采访,与冯铁健医生相识之后,在他的引荐下,我认识了小路。
初见小路,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小路的胞弟因患上艾滋病已经先他而去。小路的CD4细胞仅剩26个,他的生命正迈步走向死亡。为 此,他决定趁着生命有限的时光,用亲身经历告诉大家艾滋恶魔的可怕和他拒绝投降的勇气,甚至同意在一定时候公布他的病理日记。
其实,就在我握着小路伸过来的一双手时,一切就这样决定了,小路同意接受我的独家专访。
小路认定他的时日不多,估计不吃药治疗的话,最多只能活三个月,希望我抓紧时间采访。我们商定,从5月1日劳动节放假那天开始劳动,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谈完,每天谈三个小时。但是,由于他身体的每况愈下,到后来一天最多只能谈一个小时。加上中途有许多杂事阻碍,直到9月初才大体结束了对他的采访,前后花了6个多月。 此后,我又采访了他的妻子、医生、发廊妹等人。每盘60分钟的录音带,我用掉了38盘。
9月底,为了全程记录一个HIV患者最后的抗争,为了了解泰国HIV艾滋群落的生存状况,我和摄影师陈远忠先生一起,陪伴着小路去了泰国、老家潮阳,作一次生命的最后回访。
10月19日傍晚19时23分,在深圳市中医院的急诊室里,小路终于疲惫地合上了双眼。
小路走了。
然而,我的耳边,仍时刻想起他的那句话:不要因为我的死亡而停止我们的事业,真正对抗HIV病毒的武器,就是全人类的共同抗争,就是了解和预防艾滋。
我要感谢小路,由于他的配合,他让我找到了世界上少有的、如 此完整的艾滋病个案。
在众里寻他千百度之后,我终于面对面地逼视一个艾滋病患者,终于能够了解他的过去与现在。
我们原先约定4月25日下午2点30分在某处见面。就在那天中午,冯医生致电给我,说他已匆匆赶回老家,就在当天早晨,他身患艾滋病的弟弟撒手西去。弟弟的突然亡故,更加快了他抓紧有生之年,透过媒体吐露心声的决心。
在约定时间的三天后下午,在冯医生的陪同下,我与患者见了面。看上去,他个头中等,大约1.70米的样子,模样周正,用广东话来说,是个靓仔。他衣着整洁,是一个注重仪表、讲究礼貌的人。他与医生握手后,主动对我伸过手来,我并没有多想,也来不及多想,伸出手去,和他握了握,在那一刹那,我分明看到他的眼眶里有晶莹的泪水在闪动。我忽然明白这简单的礼节对他来说,几乎成了望尘莫及的奢侈。
在整整一个下午的采访中,我几次想洗洗手。我明显地感觉和他握过手的那只手掌心莫名其妙地发痒。在我长达14年的记者生涯中,我和各色人等握过手,也能坦然面对各种人物,今天却多少有些忐忑不安。
说到底,我多少懂得这样一个常识:HIV病毒不会通过空气和一般生活接触传播。理性告诉我不用怕,但是,真正这样近距离地面对艾滋病患者,恐惧依然无法避免。
在此之前,我尽可能地阅读有关艾滋病的报道,不断地向有关专家和医生请教,也明白艾滋病的几种传播途径,但真要与艾滋病人面对面握手交谈,在他唾沫星子飞溅下记笔记,录音,同他握手,甚至后来在餐厅请他吃饭,说实话,我都害怕得要死。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勇敢的女人,但这种害怕似乎与勇敢或怯弱无关。在人类目前仍旧束 手无策的病魔前面,因为生命的脆弱而小心谨慎地避免任何形式的接 触,也是无可指责的。握手之后,我看见同样握过手的冯医生还是那 么坦然,特别想到戴安娜王妃去艾滋病医院探望病人,并同他们握手, 我才逐渐镇静下来,随着病人的讲述,就渐渐有了几分感慨和感动。
这位先生恳请我不要暴露他的真实姓名,因为他还要在这个世界 上顽强地生活下去。我尊重他的选择。他给自己取名为“路人”,就 是过路客的意思。我说:“以后叫你小路,好不好?”他有几分感动 地点点头:“你的到来也许是我生命中最后的礼物。涂记者,我相信 你。”沉默一会,他又说